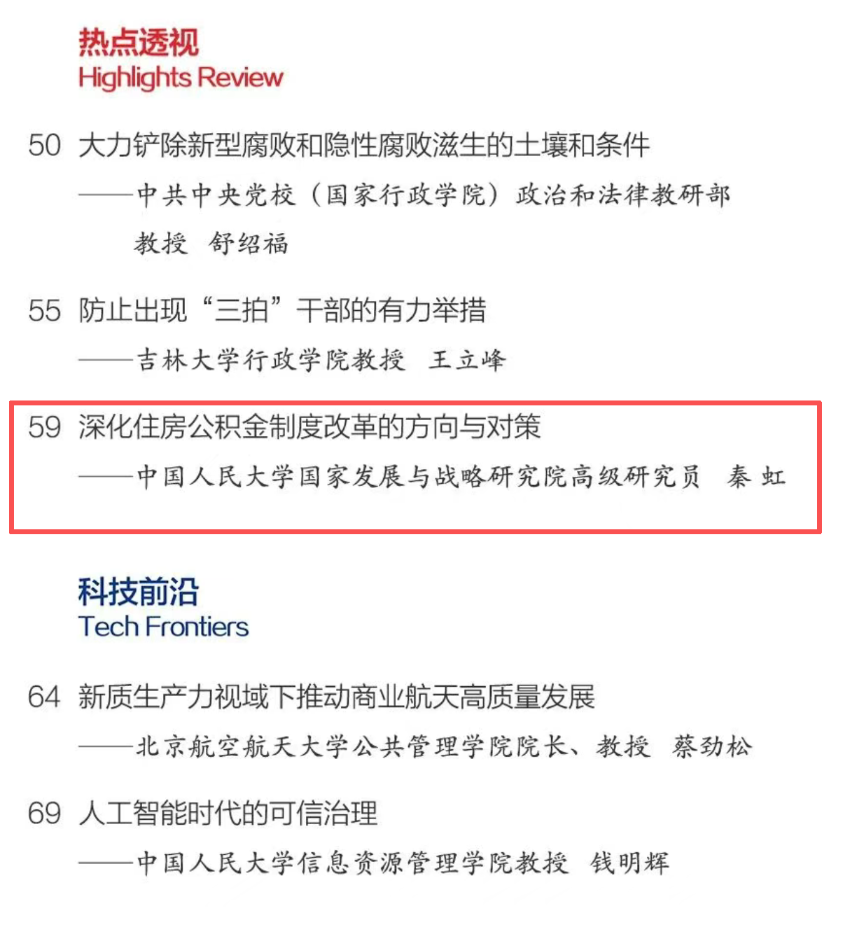[气候政策与绿色金融]代志新、张博文:绿色财税政策优化路径
发布时间:2025-11-25近期,围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一系列部署相继出台,绿色财税作为“看得见的价格信号”与“摸得着的资金约束”,其效能如何进一步释放,决定着从“项目式推进”迈向“体制化转变”的速度与质量。因此,对于如何优化绿色财政政策真正重要的不在于简单加码,而在于结构调整——用更清晰的税制逻辑、更有约束的预算规则和更可感的消费激励,推动双碳目标的实现。
一、税制优化:从强度加总到结构优化
绿色税制不仅是环境规制的重要手段,也是通过价格机制内化外部性的关键工具(Fullerton & Metcalf, 1997;Martine, 2017)。过去十年,绿色税制的“多税共治”轮廓框架已经基本形成,但在边界、税目与传导上仍存在不少的制度断点。在当前财政压力加大的情况下,不宜一味推行绿色减税的总量加码,而是适度采用微调或者助推的机制,优化绿色税制结构。
第一,资源税与消费税的“边界—税目—档次”要对齐。资源税不仅是对自然资本消耗的一种价格化约束,更是推动资源集约利用的重要工具。在设计上,应逐步在“从量为辅、从价为主”的框架内扩大覆盖面,并结合资源稀缺度、生态敏感度与开采强度实行差别化有效税负。例如,对于矿产资源,可以依据可再生性、恢复周期等稀缺性指标,对稀缺资源实行更高税率;对于水资源,则可根据流域水文条件、污染承载能力和区域生态敏感度制定分档征收标准。消费税在保持总体框架稳定的前提下,优先纳入高能耗、难降解、跨区域外部性强的产品与材料。例如,一次性塑料制品、含氟制冷剂以及高硫燃料等,都应进入消费税征收范围。对于成品油等传统能源产品,应当设置更精细的分档税率,并将非道路用油、船舶燃料和施工机械燃料等纳入差别化调节范围。具体来说,可以按照燃料的含硫量、VOC排放强度和燃烧效率等参数分级课税,让价格信号真实反映其对环境的边际损害。为降低执行难度,可建立“商品属性参数表”,将商品编码与能效标识、可回收性指标相挂钩,并设定滚动更新机制。这既利于基层征管部门操作,也能为企业提供稳定的投资与消费预期。同时,消费税改革还应与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EPR)联动,对一次性制品和低可回收性产品,结合再生材料比例、可拆解性和标识追溯度设置档次税率,实现“税收—回收—再制造”的闭环激励。
第二,增值税要把“免税逻辑”改成“抵扣逻辑”。长期实行免税政策会削弱用能单位的进项抵扣,容易导致投资激励链条中断。更合理的方式是实行“先征后退”,可以在保持税制中性的同时提供边际激励。同时,对节能设备和清洁能源关键环节,应实施留抵退税直达机制,显著改善企业现金流。例如,酒店若通过合同能源管理(EMC)模式更换冷站设备,如果其进项能够立即抵扣,留抵退税又能快速到账,那么项目的回收期会大幅缩短,投资积极性也会增强。基于此,可以引入“绿色发票系数”。即在留抵和退税环节,对经第三方或行业平台确权的绿色投入发票给予系数加权。该系数由设备能效等级、生命周期环境绩效、合规与追溯记录等综合生成。为防止套利,应设置上下限区间,并配合“事前备案—事中抽核—事后回溯”的三重机制,通过电子发票“绿色要素码”和在线监测数据进行交叉验证。一旦发现偏差,可触发季度性回溯和退付调整。这种机制既保持了增值税的中性原则,又通过数据化方式提供长期稳定的边际激励,促使企业在设备更新与工艺改造上作出“算得过来”的理性决策。
第三,企业所得税应从“项目审批式优惠”转向“税基侧组合拳”。当前的项目审批式优惠存在门槛高、周期长、覆盖面窄等问题。更有效的办法是将节能降耗、储能、能效提升等改造统一纳入投资抵免池,并与加速折旧、加计扣除政策打包实施。这样能够降低中小项目的准入门槛,让更多企业受益。同时,应建立目录动态更新与绩效退出机制,确保政策覆盖的技术与项目始终具备高边际贡献,避免形成“固化名单”。例如,中小企业如果购置节能锅炉或分布式光伏发电设备,可以在所得税环节立即享受抵免或加速折旧,从而显著降低投资成本,提高绿色改造的收益率。在车辆相关税费上,应推动购置税、车船税与消费税的统筹分档。通过排放标准、能耗水平、整备质量、电池能量密度等指标,构建一套多维度的分级体系,使“高排放多负担、低碳多优惠”的信号覆盖车辆全生命周期。例如,大排量燃油车应在购置与使用环节承担更高的税负,而新能源汽车则可根据续航能力和能效表现享受差异化优惠。在执行上,还应与“以旧换新”政策联动,建立车辆全生命周期的激励与约束机制。这样不仅能引导居民作出绿色消费选择,还能推动汽车产业链在技术迭代与结构升级中形成内生动力,兼顾环境目标与市场活力。
税制优化的核心,不是以行政审批叠加复杂性,而是以电子发票、在线监测与行业平台数据实现“可量化—可核验—可追溯”,用“连续小步、滚动评估”的方式把小改良积聚成大效果。
二、绿色财政支出:从项目驱动到规则驱动
绿色财政真正的难点不在“钱够不够”,而在“钱花得好不好”。财政支出的配置效率必须与环境目标紧密耦合,否则即便有大量投入,也可能因分散、低效甚至错位而削弱整体成效。绿色财政的有效性取决于预算编制环节能否将环境目标纳入硬约束(茆晓颖,2016)。因此,绿色财政的核心在于通过制度化安排,使公共资金与生态目标实现“同向发力”。
在中期财政规划层面,应当将节能减排、能耗强度下降、生态修复等核心环境指标系统化地纳入财政框架,将其转化为可量化、可预算的目标。这不仅有助于在顶层设计中建立明确的政策约束,也为各级政府的支出安排提供了清晰的方向,使预算编制过程本身具备环境导向。通过这种方式,绿色目标不再是附加在预算之外的口号,而是成为预算结构中的硬指标。
在项目立项与执行阶段,需要推行事前的绿色分类与预算标记,并辅以分级披露制度。绿色分类的意义在于将财政资金按项目类型、环境效益和外部性强度进行分级管理,从而形成清晰的资金投向结构。分级披露则通过信息透明和社会监督,增强资金使用的问责性与公信力。换言之,财政资金在支出过程中,不仅要“花得出去”,更要“花得明白”。这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也是一种责任约束,促使其在财政行为中融入更强的环境绩效导向。
在预算执行的末端,应当建立独立的第三方环境绩效评估与审计机制,并将其结果与次年度预算安排及项目库动态调整直接挂钩。这种“结果倒逼”机制能够形成政策的闭环,避免财政资金“撒面”浪费。第三方评估不仅增强了结果的客观性与专业性,还能通过公开透明的披露增强公众信任度,使绿色财政在社会监督下运行更加稳健。
整体而言,应当形成“目标设定—过程监督—绩效考核”的制度链条。这样的链条既保证了公共资金配置的约束力,也通过正向激励机制提升了资金使用效率。例如,在项目绩效突出的情况下,可以增加其下一年度的预算额度或优先纳入重点项目库,从而为地方和部门提供持续改进的动力。这样一种兼具学理严谨性与实践操作性的制度设计,能够真正解决“钱花得好不好”的问题,使有限的财政资金在绿色转型中发挥出更强的引导效应与杠杆作用。
此外,如何保证稳健的绿色财政支出也是一项重要命题。在我国地方财政压力日益突出的背景下,发挥好地方债务在绿色财税政策体系中的作用至关重要。
在规范地方债务融资与绿色发展关系的研究中,学界普遍强调应当通过财政制度安排明确资金用途边界与代际公平。首先,在债务使用范围方面,应当坚持资本性投资原则,即地方政府通过专项债或绿色地方政府债筹集的资金,应当限定用于经认证的绿色资本性支出。例如生态修复、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和节能改造等,而不应用于经常性绿色补贴。这种安排有助于确保债务资金真正形成可持续的绿色资产,同时通过“期限匹配”原则维持代际间的公平性,避免将不可持续的债务负担转嫁给未来。
其次,在债务规模与融资成本的确定机制上,应将地方政府的绿色财政绩效纳入约束框架。地方在绿色预算执行、项目绩效和环境目标实现方面的综合表现,可以作为决定新增债务额度、再融资资格以及债务融资成本的重要参考。如果地方在节能减排、生态修复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应当在制度安排上获得更大的融资空间与较低的融资成本;反之,则应当受到更严格的限制。这种做法通过将环境绩效与财政激励挂钩,促使地方政府在财政治理和环境治理中保持一致性预期,强化责任落实。
再次,在风险防范方面,应当在制度层面设立若干稳健性约束。例如,在项目现金流可得性、项目库建设质量、偿债准备金管理和专户资金监管等方面建立严格要求,从而实现对债务资金全过程的透明化与穿透式管理。这既有助于防止“绿色名义、灰色项目”的混入,也能够降低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同时,还应当考虑地区间发展水平与财力状况的差异,通过中央转移支付、政策性再贷款和财政贴息等配套机制进行调节与平衡,使财政能力有限但绿色任务繁重的地区获得适当支持,而绩效表现突出的地区则得到奖励。如此安排有助于提升资金配置效率,避免在绿色转型过程中加剧区域发展不均衡的状况。
总体来看,将地方债务管理与绿色绩效评价相结合,能够在财政纪律与环境治理之间建立内在联系。债务融资不仅仅是地方筹资的工具,更能够成为衡量其绿色治理成效的重要镜像。通过透明的规则、可量化的标准和制度化的监督,国家层面可以在确保债务安全的同时,推动绿色转型目标的实现,从而兼顾财政可持续性与生态可持续性。
三、绿色消费:让居民看到“可兑现的绿色帐”
在绿色转型的过程中,生产端的技术进步虽然至关重要,但往往存在投资大、周期长、外部性显著的特点,难以单兵突进。因此,消费侧的行为选择、偏好塑造与扩散效应显得同样关键。当前我国绿色财税政策更多集中在供给端,而居民绿色选择的直接激励仍显不足,导致消费环节在推动绿色转型中的潜力未能充分释放。基于此,亟需构建一个系统化的激励体系,将“税—补—信贷—以旧换新”等系列碎片化政策贯通起来,从而实现对居民绿色消费的全链条支持。
在具体政策设计上,可以在消费税结构微调的基础上,引入以旧换新政策与分场景消费券的组合,针对节能车辆、高效家电、绿色建材与再生产品形成“低门槛、小额、多频次”的激励矩阵。这种安排能够增强居民的“可感性”,让绿色选择从价格上更具吸引力。同时,还可以在地方层面叠加非价格类政策工具,如路权、停车优惠、物业费用减免等,以营造绿色消费的综合性激励环境。这些措施不仅增强了政策的贴近感和可操作性,也通过“到手可感”的收益提高了居民参与的积极性。
第二,构建“家庭绿色权益账户”。该账户通过电子发票、能效标识、回收凭证等多源数据,对居民的绿色购买、以旧换新与绿色出行等行为进行确权,并构建为可视化信用积分。这些积分可以与财政与公共服务挂钩,例如用于抵扣部分地方性收费、兑换公共服务额度,甚至作为绿色信贷利率优惠的依据。商业银行与互联网平台可以围绕该账户开发“消费侧绩效—信用”联动的金融产品,通过小额普惠融资与分期利率优惠提升绿色消费的可负担性与可持续性。学理上,这种安排实质上将消费侧的正外部性内部化,使绿色行为能够产生直接的经济回报。
消费端的激励若能与数据确权和积分挂钩,将有助于实现外部性的内部化(Thøgersen, 2010)。在积分机制的具体设计中,应考虑激励与约束的平衡。为避免“搭便车”行为,可以设定积分按季度动态结算,并依据产品寿命周期、使用强度进行加权修正。对“回收—再制造”的闭环行为给予额外加分,不仅能够延长产品生命周期,也能推动再生资源市场的发展。这一系列措施能够在居民“买绿色—用绿色—回收绿色”的行为链条上形成正向循环,进而在消费侧推动绿色转型的扩散效应。
然而,数据的可信性是这一促进绿色消费体系有效运转的前提。应在隐私保护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核验标准与接口规范,使得发票、能效标识、回收凭证等数据能够在财政、税务与商业机构之间互认互用。只有当激励与真实行为挂钩,绿色消费才能从政策口号转化为家庭账本上的实际收益。对于公众而言,这意味着绿色选择不仅仅是价值观念的体现,更是一种可核算、可兑现的经济行为;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则意味着绿色消费政策从象征性倡导走向实证性、制度化运行。
进一步地,绿色消费不仅是居民个体选择的问题,也与产业链升级和市场结构优化紧密相关。通过消费端需求的聚合,可以形成规模化的市场信号,倒逼企业改进生产方式和产品设计。例如,当节能家电或新能源汽车在市场上形成稳定需求时,制造商将更有动力加大研发投入和技术迭代,这种“需求拉动”效应能够与“供给推动”形成良性互动。此外,绿色消费还能带来社会文化层面的扩散效应。随着绿色产品逐步进入日常生活场景,公众的消费习惯、社会认同和价值观念也会随之转变,推动绿色生活方式从少数群体的选择扩展为普遍的社会规范。换言之,绿色消费不仅是经济行为,更是社会转型的重要切口。
四、制度协同与治理机制:从单点政策到系统集成
绿色财税政策不仅仅是财政和税收部门的事务,更是跨部门、跨层级制度协同的重要组成部分。跨部门信息共享和联合问责是绿色财税政策走向系统集成的关键(石英华,2023)。只有在治理体系中实现横向协调与纵向联动,政策工具才能真正落地并发挥乘数效应。当前的政策执行中,仍存在部门间信息壁垒、地方与中央政策口径不一致以及监管碎片化等问题。解决这一困境的关键在于推动财政、税务、生态环境、能源等多部门之间的联动治理,建立起数据互认、政策互补和监管互通的机制。
首先,在信息共享机制上,应推动税务征管数据与生态环境监测数据的深度对接,并实现跨部门的动态共享。例如,持续推进将环境保护税的征收环节与污染物排放监测平台实时联动,不仅能提高征收效率,也能增强政策的约束力和精准性。财政部门的预算执行数据则应当与绿色绩效评估结果挂钩,做到资金流与绩效流相统一,避免“钱花出去了、绩效难以验证”的情况。与此同时,还可以推动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建立统一的绿色数据接口规范,确保地方提交的财政与环保数据具有可比性和可核验性,从而提高宏观政策评估的科学性与透明度。
其次,在政策协同机制上,绿色财税工具应与产业政策、金融政策乃至区域发展战略形成合力。例如,财政支出支持的绿色项目,如果能够同步获得绿色金融产品的配套融资,不仅能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也能形成“财政+金融”的双重激励,提升绿色投资的可持续性。税收优惠政策与碳市场机制也应当协同推进:前者降低绿色转型的边际成本,后者通过市场化交易形成动态价格信号,两者的结合能够显著提高政策有效性。此外,绿色消费政策、绿色信贷政策与绿色政府采购也应当在执行层面联动,使公共部门、金融部门与社会部门形成一致的政策预期,避免政策工具之间出现“打架”或“空转”。
再次,在监管与问责机制上,应建立跨部门的联合绩效考核与监督体系,将绿色财政支出、绿色税收征管、地方债务使用和消费激励等指标统一纳入综合治理框架,并与干部政绩考核、财政奖惩制度直接挂钩。这不仅能提升政策的执行刚性,也能形成制度性的责任约束,防止绿色财税政策在基层执行中出现“选择性落实”。为提高问责的客观性,可以引入第三方独立评估机构和社会监督机制,强化数据的透明披露和绩效的社会检验,从而在政策执行中形成“硬约束+软监督”的双重机制。
总体而言,制度协同与治理机制的完善,意味着绿色财税政策不再是孤立的政策工具,而是嵌入国家整体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横向的部门协作与纵向的中央—地方联动,可以推动形成一个以数据为基础、以规则为核心、以绩效为导向的系统集成格局,使绿色财税政策从单点突破走向全面协同,真正发挥出推动绿色转型的战略引领作用。
(作者代志新,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财政金融学院教授,行为实验财税研究中心主任;张博文,系中国人民大学行为实验财税研究中心研究员)
原文链接:[气候政策与绿色金融]代志新、张博文:绿色财税政策优化路径
参考文献:
1.Fullerton, D., & Metcalf, G. E. (1997). Environmental Taxes and the Double Dividend Hypothesis: Did You Really Expect Something for Nothing? Chicago-Kent Law Review, 73(1), 221–256.
2.Martine, M. O. N. Z. A. (2017). Environmental Fiscal Reform: Progress, Prospects, and Pitfalls.
3.Thøgersen, J. (2010). Country Differences in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The Case of Organic Food. Journal of Macromarketing, 30(2), 171–185.
4.茆晓颖.绿色财政:内涵、理论基础及政策框架[J].财经问题研究,2016,(04):83-87.
5.石英华,刘彻.绿色预算的理论内涵、国际借鉴与中国制度构建[J].经济纵横,2023,(08):107-116.